金边步行街地摊火热,中国同胞开始涌入抢占市场?
2024年12月,一名来自中国的小伙儿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代广场火了起来:他仅凭5个英语单词就跑到了美国去卖玩具,在抖音上发了6个短视频涨粉60多万,立刻在中美两国的社交媒体上成为了一名极具流量的“网红UP主”。

上图:阿才在摆摊,左边为本地顾客
而他通过叫卖的方式在纽约时代广场向老外推销“爆眼龙”捏捏玩具,推销交流过程中无论老外问什么,博主只会使用“吐刀乐、吐刀乐”(two dollar)等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,因此还被广大网友称为“刀乐哥”,甚至不乏有人也想效仿他来到美国赚上一笔:毕竟“刀乐哥”买的小玩具,在国内也就几块钱人民币,却被他在纽约卖出了2美元的“天价”。
可那一张小小的美国签证,却给所有想效仿“刀乐哥”的网友们泼了一盆凉水:因为拿下美签存在一定的门槛,而且能够拿下美签也意味着申请人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,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像“刀乐哥”一样去卖小商品;而与中国只有2000公里左右的柬埔寨,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门槛,而在潮汕小伙儿阿才看来,这也是他在柬埔寨摆摊看到希望的地方。
第一次摆摊:他遇到了义务帮忙的本地高中生
2023年年初,阿才抵达柬埔寨金边。那时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,也没有创业的打算。他来这里,是因为“想换个地方看看”。
“就是来旅游的,当时在国内做点小生意,刚好有段空档,就想着到柬埔寨看看。”阿才告诉记者,“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了想留下来的想法,也说不上是为了生意。当时没有那么明确的商业目标,就是觉得这里的氛围好。你看他们都可以摆摊,卖吃的、卖衣服、卖东西,没有人来撵你。”
这种“敢”,不是冲动,而是一种职业直觉:阿才对什么东西能卖、怎么卖,有着天然的敏感度,柬埔寨街头随处可见的摊点与流动商贩,让他意识到:这里并不排斥“草根经济”,而这可能是一种机会,于是在跟妻子商量之后,阿才决定来柬埔寨“试一试”。
阿才介绍,自己的货源来自潮汕本地。“我老婆的闺蜜是开工厂的。”他说,“化妆品拿货不难,什么洗面奶、面膜、护肤套装,我都可以从她那里直接拉货,然后小批量发往金边,成本可控。”不过,真正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层面:身份、语言,以及文化。

上图:阿才摆摊之初,主要售卖化妆品
阿才选择摆摊的地方是金边王宫边上,这里是柬埔寨的一个景点,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湄公河边散步游览;但在本地人眼中,一个面孔陌生、言语不通的中国人出现在摊贩之间,仍旧是异常的存在。
“刚开始去摆的时候,确实感觉到周围人看我眼神是有点不一样的。”阿才回忆,“他们都在想,怎么来了个中国人在这边摆摊?”这种“异样”并非敌意,而是一种混合着好奇与防备的观察。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语言障碍。
“我不会柬文,基本一句都不会讲,一开始我就用纸写几个词,贴在摊位上,人家问价,我也听不懂,只能比手画脚。”阿才说,“后来就是突然来了几个会中文的本地高中生,帮我解决了沟通问题,而他们也是义务帮忙没找我要一分钱,就在这里帮我直到我收摊。”
除了语言的意外补位,令阿才印象更深的,是本地摊贩的态度。
“他们不会排斥你。”阿才说,“你一个外国人在这摆摊,他们不赶你,也不抢你。他们还会帮你,有时候我不懂价格,隔壁的摊贩会帮我讲。有一次我没零钱,人家还帮我换钱。而在国内摆摊你可能得提防同行、提防城管、提防投诉;在这里,你不会有这种感觉。”
靠着这些“小幸运”,阿才的摊位慢慢运转起来。他卖的是化妆品单价不高,但利润可观。
“做得最好的一天,是送水节那几天。”阿才说,“人特别多,我那晚一个人就做了快300美金。”平常周末,他平均每晚收入在80美金左右,“60至70美金是常态,能卖一点就算成功。”

上图:本地顾客在阿才的摊子前挑选商品
这笔收入对于他来说,不仅仅是金钱,更是一种验证:在一个陌生社会里,只要环境允许,哪怕是语言不通的“外人”,也可能靠最基础的劳作获得生存的空间,那段时间,他第一次意识到,在一个制度相对宽松、文化相对包容的地方,摆摊本身,也可以是一种体面且自由的生活方式。
“后来有很多人加我微信、抖音,问我能不能教他们在柬埔寨摆摊。”阿才说,“我都告诉他们可以摆,不收费,管理也松。我说你们可以来试试。”
“破天富贵”袭来:他看到了中国人“暴富”的可能和希望
而到了2024年底,阿才已经不再摆摊,后来他就开了一家名叫“大侠煲仔饭店”的餐馆,而这个名字也是他的粉丝帮忙取的。确实忙不过来了。”他说,“不是不想继续摆,是实在腾不出人手。”
可即便如此,阿才并没有完全抽离这个街头经济的世界,因为湄公河边那里依旧是他创业的起点,特别是金边市政府宣布将这里在周末划为步行街后,阿才在交谈中告诉记者,如果以前是摆摊只是赚点兼职收入,那现在很有可能大家会有一种“暴富”的可能和希望:因为在步行街开放的周末两天,金边绝大多数的人流就集中在这个区域。
“现在摆摊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,”阿才告诉记者。
这并不是主观印象。据他粗略估计,现在在步行街附近周末出摊的中国人至少有十几组,大多是兼职。“有的是有工作,只是下班了来摆,有的是陪家人来柬,闲着就干一份。”阿才提到一位印象深刻的安徽男子,“他女儿在这边教书,他就陪女儿过来。没事干他就出来摆摊。”
但更让他在意的是:摆摊的模式,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。
“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出来卖。”他说,“现在开始有中国人请本地人去卖,自己当老板,在后面供货就行。”这个“后退一步”的动作,正悄悄改变整个摆摊生态。
“比如一个摊子,一晚上生意不错的话能卖到100多美金。那你给本地人10到20美金,让他帮你卖,剩下的钱你就坐着收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,却道出了一个关键逻辑:用极低的雇佣成本撬动稳定现金流。

上图:阿才现在经营的大侠煲仔饭
根据他描述,这些被雇的本地人,多为年轻人或临时劳工。“你给他十美金,他就很开心了。他们本地正常一天工资也就这个数。”更重要的是,这些柬埔寨摊工不太计较分红、工时,只要每天能结算现金,就算满意,“有的甚至不讲条件,你让他站哪儿他就站哪儿。”
而摊位本身,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“市场摊铺”。
“步行街目前并不强制收费,大摊位可能需要30美元租金,但一般情况下,只要你找得到空位,不占别人老位子,没人会撵你。”阿才说,“先到先得,还是这个理。”
在这样的环境下,摆摊开始变成一种“轻资产、可扩张”的小型经营模式。许多做得早的中国人,已经从“自己吆喝”变成“雇人站岗”,一个摊位变两个、两个摊位变四个。
“这些之前摆摊的中国人自己不摆了,就找几个柬埔寨人替他跑,他在定期供货。”他顿了顿,“有时候甚至不用他自己去,他直接找人管。”
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“摆地摊”,更像是一种微型渠道分销网络。而在人力成本低、监管宽松的金边,这样的模式具有现实的扩展土壤;这一切之所以成立,得益于几个关键变量:租金低(有时候没有)、人流大、监管宽、劳力便宜。
另一方面,政府方面的管理人员一般只对大音响、占道过大等行为提出温和提醒;“他们不会乱收钱,更不会扣你货。”阿才说,“顶多就是礼貌地告诉你‘这个地方不能摆’,你换个地方就好了。”某种意义上,这就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创业平台。
阿才透露,摆摊虽然简单,但它是一种最贴地气的观察方式,能看到什么产品火,谁在买,价格弹性多大,这些东西,坐办公室是看不到的。
而记者问及目前中国人在柬埔寨摆摊,未来会不会多赚点钱”成为“摊贩资本家”,阿才表示,想在柬埔寨小成本试水,摆摊绝对是个入口;他说:“说不定再过几年,这条街上的摊位,就都被中国人包了。”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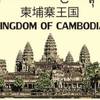





 游客
游客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